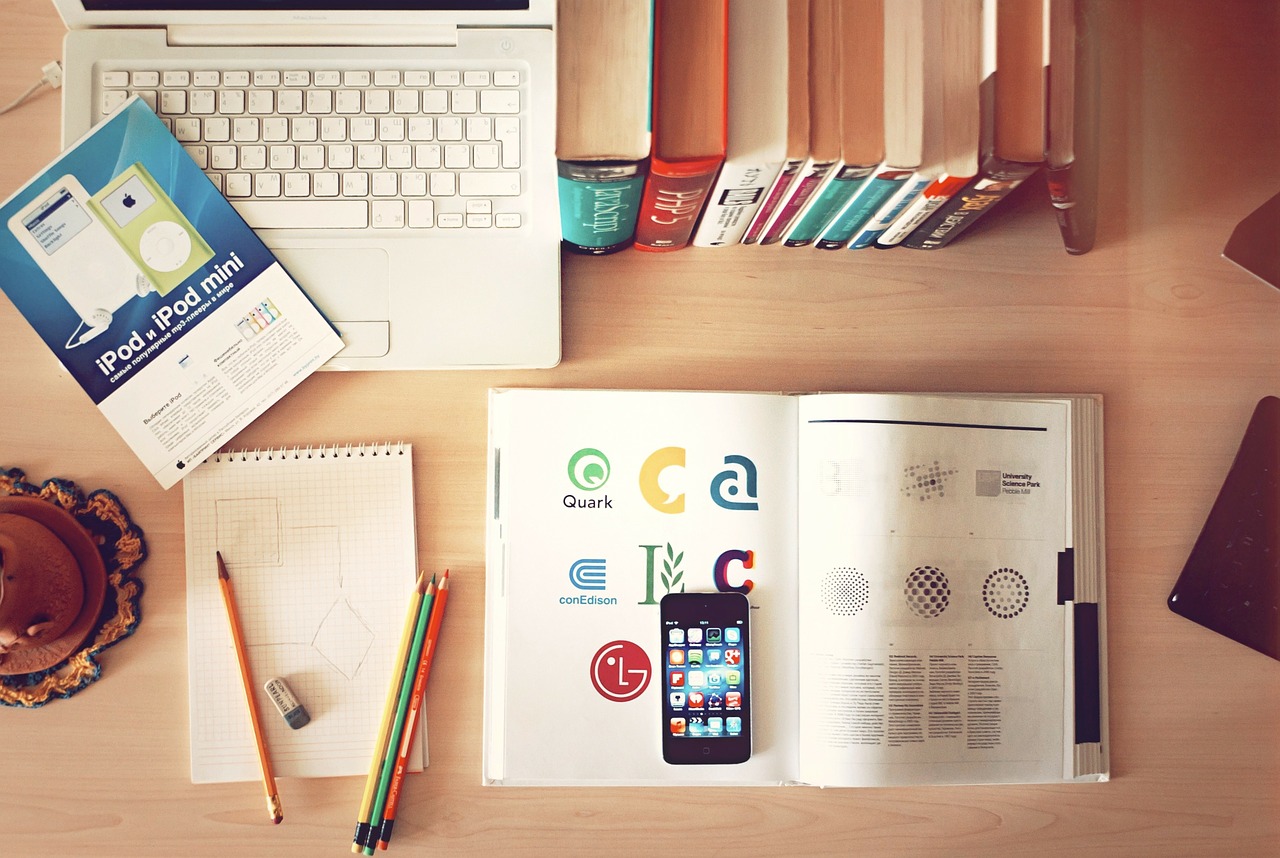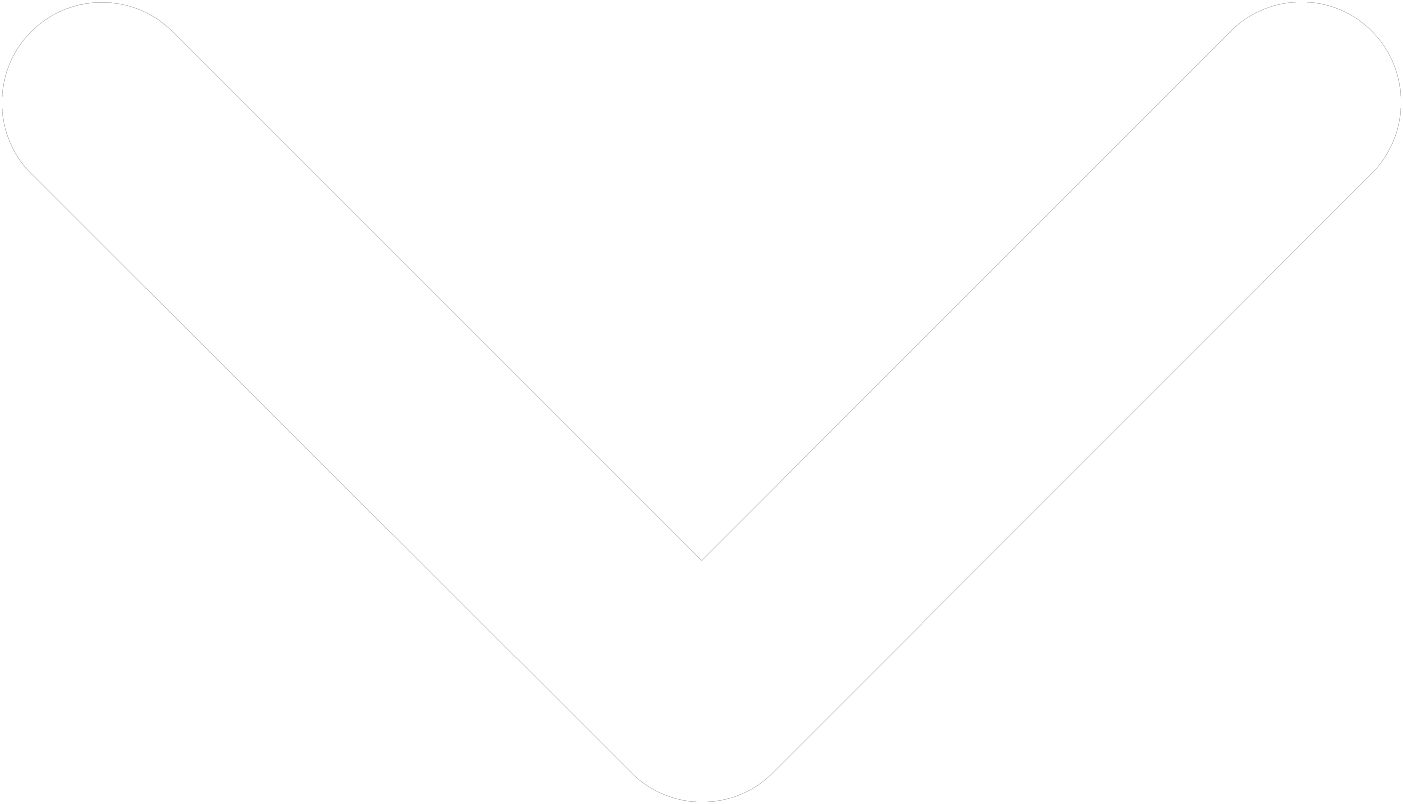改革中跟留学生相关的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学生签证审核收紧:
1.加强院校担保(sponsor)合规要求:所有持牌院校须保持≥95%入学率和≥90%课程完成率;
2.强制“中介资质框架”(Agent Quality Framework):所有使用海外中介的院校,必须注册并接受该标准的审计;
3.毕业生毕业后工作签(PSW)时长从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进一步压缩留英就业窗口;
二,工签门槛大幅提升:
1.签证的学历要求直接从RQF Level3(ALevel高中毕业)跃升至RQF Level6(大学本科毕业);
2.对应的最低年薪门槛大幅上调;
3.原有的“短缺职业清单”的工资优惠取消;
三,英语语言要求提高:
1.技术工签英语要求从CEFR B1(日常交流)提高至B2(流利沟通);
2.所有随行家属(工签及学签)首次申请须达A1(简单沟通)水平,延期时须达A2(基本沟通),申请定居时须达B2;
3.大多数定居签证的语言门槛由B1提高至B2,融入标准在各类签证中保持一致;
四,定居与公民政策改革
1.永久居留(ILR)获取所需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并引入“积分加分”机制,根据个人的经济与社会贡献决定获批优先度;
2.公民身份申请纳入积分制,在满足规定贡献后可获得加速路径;仍保留5年路线,适用于英籍人士的非英籍直系家属;
总结一下,让移民“先证明贡献、再获得权利”——是这次政策的核心理念。这与丹麦等北欧国家模式趋同,即用延长永居时间+提高标准,筛选出更愿意融入、稳定缴税的移民。据内政部的估算,新的恢复移民控制政策将减少10万移民。移民问题一直是令英国头疼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和人口结构依赖新移民补充劳动力和人才;另一方面公众和政治对移民规模表现出强烈担忧,每次大选的时候,移民总是最被关心的话题之一。在过去十年中,英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经历了剧烈反转。
1.2010年代初:强调“吸引全球人才”,国际学生被归为“软性移民”;
2.2016年脱欧公投后:反全球化情绪上升,“控制边境”成为广泛共识;
3.2020年后疫情时代:公共资源紧张、生活成本上升,移民再次成为替罪羊。
根据英国官方数据,2023年英国净移民人数高达90.6万,上一年是72.8万人,再加上数量不详的非法移民,已经远高于英国脱欧前的平均水平,对社会福利系统(NHS、住房、教育等)的压力持续增加。
同时,在英国媒体与右翼政客的推动下,大量报道将“硕士带配偶”、“印度/尼日利亚留学生毕业后不回国”(确实约3~4%非欧盟学生在签证到期后未被记录离境,其中,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在“合法入学—非法逗留—申请庇护”链条中占比偏高)等情况与非法移民、社会资源挤占挂钩,引发了公众对“教育系统是否沦为移民跳板”的质疑。
英国不是不要移民,要的是能为英国做出贡献的移民,留学生本来可以成为符合英国需求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留学生=移民通道”的叙事被不断强化,毕业生签证(PSW)本来是测试留学生是否可以、是否合适留在英国的试金石,被强制从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留学生又一次成为了移民政策的牺牲品!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严格控制移民的同时,政府在庇护体系内部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和费用失控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解决,2023年获批“政治庇护”及其他保护形式的总人数达到了20888人,签证逾期、小船渡海等各种方式的非法移民纷至沓来,积压的庇护申请已超过13万份、超过22.47万人,政府还不得不用大量的公帑来为他们提供条件优渥的食宿,2023/24财年仅用于庇护申请者的食宿费用就高达47亿英镑,催生出了格拉汉姆-金(Graham King)这样可以通过难民安置公司“创业”、日入480万英镑的励(che)志(dan)故事。“恢复移民控制”不只是一个政策口号,它揭示了当前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教育价值与政治博弈之间的激烈张力。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或许是最无声却被牵动最深的角色。